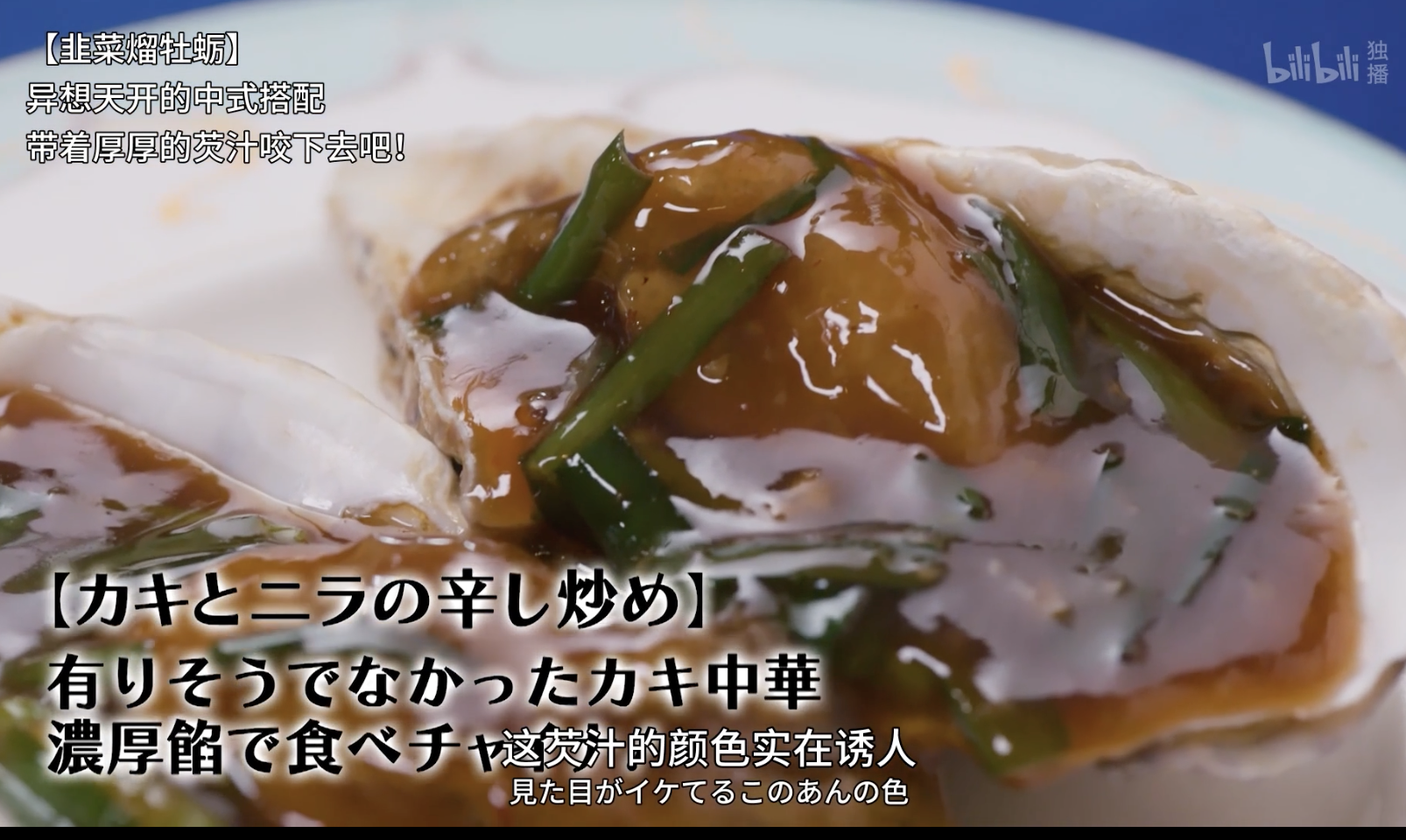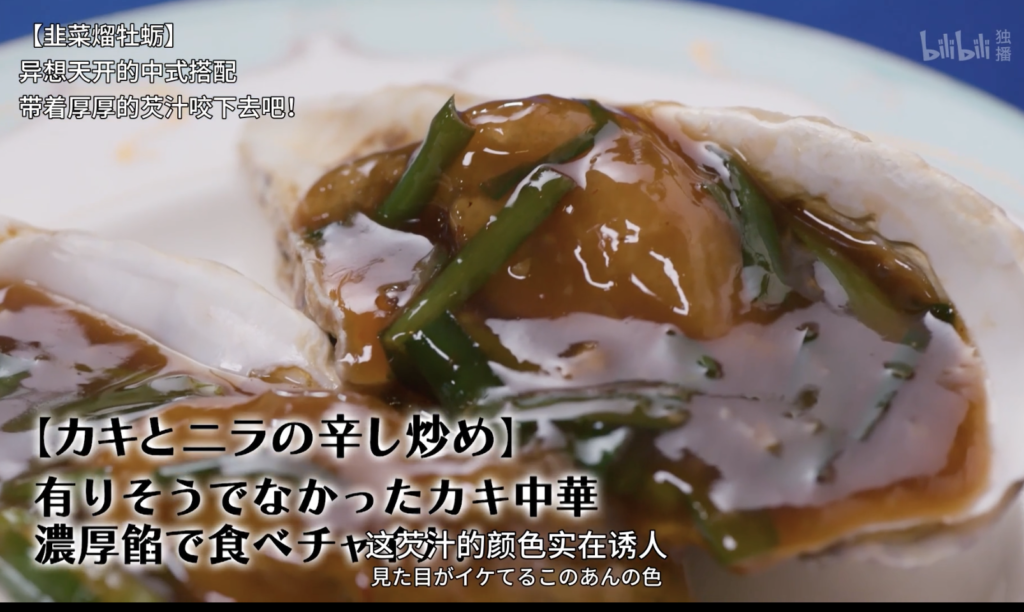一
1944 年末,虽然二战还没有结束,但不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东方的太平洋战场,德军和日军实力都已遭到重创。战争胜利曙光乍现,时任总统罗斯福已经开始计划战后国家战略的规划问题。
罗斯福总统给当时担任白宫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负责人的范内瓦·布什发了一封信函,希望能筹备一份关于美国科学政策的报告。
范内瓦·布什是工程师出身,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麻省理工大学工作,他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担任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的顾问,直接领导了美国军方包括原子弹、军用雷达在内一系列黑科技的研发。
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虽然在战争期间美国的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突飞猛进,但这大都关于军事。由于战争,许多研究者其实都中断了之前的研究,而且当时在美国的许多科学家都来自欧洲或其他海外国家,现在战争要结束了,美国必须要在战后科学研究方面的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罗斯福总统主要关注的方向有四个:一是让实现科技军转民以及解决就业问题,二是如何推进医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三是处理好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组织之间的关系,四是对科学研究人才进行规划。
第二年七月,范内瓦·布什回复的报告在二战结束前夕发表,就是这份《科学:无尽的前言》。
这份报告为美国二战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份报告规划的框架下,美国这几十年来取得了远超二战结束时候的成功,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摆脱了对欧洲的依赖,称霸全球。
二
在这份报告中,布什首先肯定了科学研究的地位。他认为科学研究会带来新知识,那是所有实际知识的源头活水。在和平时期,科学研究能给人们带来健康、带来更丰富的商品更多就业岗位等等,“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人类对这个世界上知识的求知欲,没有任何人能够精确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有意思的地方是,微软中国 CTO 韦青在评论中提到,战前的布什博士在军事技术上至少有两点判断错误,一是他大大低估了导弹技术的前景(也让钱学森有了回到中国的机会),二是他在战时拒绝给电子计算机项目拨款,因为他不相信电子计算机能很快的被制造出来。
不过工程师出身的布什博士非常清楚的知道人在科学研究面前的局限性,他不遗余力的坚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家的自由。这份坚持非常不容易,毕竟科学研究只属于小部分人,大众很难理解政府将他们的税钱撒给一群没有目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疯子们。
战争的经验让布什意识到,科技的奇迹依赖基础研究,然而基础研究无法考虑实用性的目的。即使这与大众的期望冲突,他还是在报告中写道:“科学进步本质上依赖的是科学家无需考虑实际目的的自由基础研究。”
布什认为这种研究注定只属于一小撮聪明的科学家,他们主要存在于各大专院校中。
布什拒绝让政府领导科学研究机构,希望成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独立于政府,制定和推广科学研究的相关具体政策。政府的职责,是要成为大众和那帮精英科学家之间的桥梁。
布什的另一项设计,是专门设立独立于军事机构的军事科学研究的文职机构,把军事科学研究和士兵训练分开。
另外,布什实施了军事订货计划,让政府采购大学、产业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创建政府的实验室,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催生了美国“军事-产业-大学”的铁三角联动体系。
布什还认为科学研究成功要尽可能公开化,特别强调了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与和合作,专门成立部门帮助出版和交流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研究成果的全球交流。
事实上,直到报告发表5年后的1950年,布什设想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才正式成立。政府被设计成了一个从事科普活动的角色,政府要投入并鼓励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也要教导大众采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还要想办法采取措施让大众有能力领取弹药——享受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话题,是对科学本身范围的定义,除自然科学、医学外,社会科学是否算得上科学,在这一点上布什异常坚定的认为:“以牺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他对国民福祉至关重要的研究为代价来发展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但是说归说,实际上布什还是将社会科学排除在外,理由是他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中与政治和政府联系太过紧密。
从这点可以看出来,排除政府对科学家的影响,是布什博士放在第一位的。
这种完全自由的研究环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优秀科学家们。尤其是是在二战之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为美国之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宝贵的人才基础,可能这才是这项政策的最大意义所在。
三
这个框架也并不完美。如果熟悉苹果公司历史的话,一定会对加州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有印象,Macintosh 的设计灵感就来自那里,激光打印机、办公室局域网、激光CD光盘等等一系列技术也都来自于这个实验室。这个著名的实验室,研究方向是“信息架构”,它正是政府资助的实验室之一。
实际上不论是乔布斯还是盖茨,对施乐实验室的评价都偏负面——一群很厉害的科学家,浪费了很多钱,搞出了一大堆炫酷但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很有代表性,凡是政府出钱做事儿,就多少会效率低下。政府注重基础研究,自然就挤压了应用研究方面的资源。
在报告提出的 1945 年,科技水平并不发达,大多数应用类发明都还很原始,枯燥等待着基础科学的突破。但到了1960年代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被发明出来之后,应用类的研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基础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用科学的研究就只能依赖于那些私营企业,这类研究往往更加商业化,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与基础科学研究脱节。
政府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无法满足市场要求,私人资本只好自己来,但私人资本又离不开政府订单的帮助。
一个例子是 NASA 花了很多年,才得以让私有企业参与类似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的投标。2009 年,虽然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的火箭发射效率远超过原先政府资助的那些火箭发射供应商,但 SpaceX 原先根本无法获得政府订单,后来还是在经过诉讼美国空军后,才得到了火箭发射的订单。
这种体制性问题制约了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到 2015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私营部门为基础研究提供的资金已经超过了政府。甚至在 5G 时代,美国在一些领域的研发能力已经开始落后中国(然后就开始了贸易战和科技战这样的手段)。
这种脱节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注意,199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唐纳德·斯托克斯发表了《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提出强调应用驱动的基础科学研究。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直接对原来的框架进行了批评。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科技公司也已经在美国经济有了极高的地位,知识工作已经成为了主流,而且私人资本无比壮大,基础科学研究似乎的确更加有机会与产业结合,主动掌握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完全随机的“瞎猫碰死耗子”。
科学家需要自由,但同时政府需要方向。
2020年,美国出台了《无尽的前沿法案》,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中心从之前的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转向了支持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和支持区域技术中心的建设。政府希望更加定向去补贴特定的研究方向,这也是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出台以及对针对中国开展“科技战”的主要背景。
四
对科学知识的探索,需要自由的灵魂,这似乎是一件浪漫的事,但科技与军事息息相关,竞争总是刺刀见红的。
大众和科学家之间,总是隔着一层玻璃,但科学家最终也是普通人,而其他普通人也需要享受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当下能运行的最好方案。